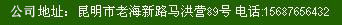|
我国知名研究白癜风的专家 http://m.39.net/pf/a_5941786.html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举办的“古典教育研讨会”(年11月)上的主题发言,经扩充后以“世界史意识与古典教育”为题刊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年第1期),本版经作者重新拟题及稍有增订。感谢刘小枫老师和”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公号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转载推送。 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亲身经历过这一伟大历史变革的学人抚今思昔,都会对我国学界经历的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感慨万千。年的“我们”在读什么书、能读到什么书?当时尚且年轻的“我们”在想什么问题,脑子里有怎样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视野?如今,“我们”在思想学问和政治觉悟两方面有了多大长进?晚近20年来,我国学术景观变化之快,即便已经成为学界中坚的“70后”和“80后”学人,恐怕也有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感觉。 五四运动 自年代以来,为了应对现代列强的进逼,深入认识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迄今仍是我国学人无法卸下的时代重负。一百多年来,国家接连遭遇共和革命、内部分裂、外敌入侵和封锁围困,数代学人很难有安静的书桌和沉静的心态面对纷然杂陈且蜂拥而来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生存状态逐渐改善,学界也在不断拓展学术视野。尽管学术热点数次更迭,教育面貌不断更新,但“西学热”始终是主流。仅举荦荦大者,自年以来,我们至少经历过“经济学热”“现代哲学热”“社会理论热”“后现代哲学热”“古典政治哲学热”。晚近10年来,随着我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面临新的挑战,又迅速出现“世界史热”(晚近5年来尤为明显)。 这会是最后一波“西学热”吗?很难说。但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一波“西学热”都会对我国人文-政治教育的品质产生影响。与其想象我国学界还会在哪个学问领域开放自己的学术视野和学问意识,不如审视一下正在兴起的“世界史热”与人文-政治教育的关系,或者说审视我们正在形塑什么样的世界历史意识。毕竟,与其他学科的“西学热”相比,“世界史热”与我们的人文-政治教育的关系更为直接。 年,时年30岁的尼采(-)作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授出版了第二篇“不合时宜的观察”(写于年)。这篇题为“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的小册子一向被视为尼采关于史学的论著,其实,它的真正主题属于如今的教育学,因为其问题意识是新生的德意志帝国应该形塑什么样的人文-政治教育。[1] 尼采(-) 尼采写下这篇文章时,德语学界的“世界史专业”已经发展成熟,而且与巴塞尔大学史学教授布克哈特(-)开设的三次“史学研究导论”课(-)直接相关。[2]尼采对这位前辈和朋友十分敬重,但他仍然忍不住提出警告: 我把这个时代有权利(mitRecht)为之骄傲的某种东西,即它的史学教育(historischeBildung),试着理解为这个时代的弊端、缺陷和贫乏,因为我甚至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患上了一种折磨人的史学热病(denhistorischenFieber),而且至少应当认识到我们还有这种病。[3] 尽管这话在今天会让我们难堪,但我们要理解这一刺耳之言的含义却并不容易:尼采为何认为新兴的史学教育对国家的人文-政治教育会带来致命危害? “世界史”诞生的地缘政治含义渴求来自身体的需要,晚近的“世界史热”明显出自国家身体变化的需要。随着我国在经济上成为世界大国,重新认识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自然会成为我国学界的身体需要。 在我国大学的文科建制中,世界史专业迄今相当纤弱,明显不能适应国家成长的需要。年,教育部将世界史专业从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但这个专业显然没可能短时间内变得强健。我们值得问:推动晚近世界史翻译热的有生力量从何而来? 在大学任教并从事研究的世界史专业人士大多在国别研究或区域研究的海量材料中辛勤耕耘,凭靠现代社会科学的各种新派方法积累实证成果,不大可能成为这股世界史翻译热的有生力量。反过来说,由于专业划分明细,且受人类学/社会学方法支配,世界史专业人士未必会感觉得到,自己的学问意识、研究取向乃至学术样式正面临严峻挑战。 在18世纪启蒙时代的欧洲,“世界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才初见端倪。德意志哥廷根学派健将施洛策(AugustLudwigvonSchl?zer,-)40多岁时,为了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受过教育的“有学养的女士”(gelehrteDame),在年出版了《为孩子们准备的世界史:少儿教师手册》(第一卷)。[4]该书算不上西欧学人的第一部“世界史”,但它可能算得上第一部德语的为青少年编写的世界史教科书。两年后(),捷克的天主教修士、教育家帕瑞切克(A.V.Parizek,–)也出版了一部德文的《给孩子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fürKinder)。由此可见,现代文教刚刚形成之时,世界史就成了重要内容之一。[5] 施洛策首先是研究德意志帝国史的专家,同时也是德意志学界研究俄国史的开拓者。这意味着,“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在其诞生之时就与欧洲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有内在关联。 希罗多德(约前-前)在西方有“史学之父”的美誉,他的《原史》尽管在今天的实证史学家看来有些不靠谱的“八卦”,却因探究“希波战争”的成因和过程而成了今人能够看到的人类有记载以来的第一部“世界史”。[6]这提醒我们应该意识到,“世界史”的含义首先并非指编年通史,而是探究人类不同政治体之间重大地缘冲突的成因、过程及其影响。不用说,随着历史的演进,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与此相关的纪事性探究也越来越多。 希罗多德(前–前) 尽管如此,并非每个经历过重大政治冲突的政治体都留下过这类“史书”。记住这一点,对我们眼下关切的问题不能说无关紧要。 18世纪的施洛策既研究本国史,又研究他国史,难免会对“世界史”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解,这样的史学家在欧洲并不少见,而在我国学界迄今屈指可数。这并非不可理解,因为,“世界史”作为一门史学专业的形成与两件历史大事相关,而我们对这两件大事的反应都过于迟钝。 首先,历时三个世纪的地理大发现(15世纪末至18世纪末)给欧洲学人带来了整全的世界地理视野。[7]19世纪的法国有个献身少儿教育的作家叫凡尔纳(–),他的好些作品最初发表在《教育与消遣杂志》(Magasind’éducationetderécréation)上。笔者上高小时读到过他的《海底两万里》(中译本),但直到接近退休年龄才知道,他还写过给孩子们看的三卷本《发现地球:伟大的旅行与伟大旅行家通史》(Découvertedelaterre:Histoiregénéraledesgrandsvoyagesetdesgrandsvoyageurs,-),让法国人从小就知道公元前5世纪至19世纪的两千多年间那些著名旅行家和航海家的事迹,凡尔纳也因此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8]该书中译本与原著相隔足足一个多世纪之久,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 地理大发现 第二件世界历史上的大事更为重要:在施洛策身处的18世纪后半期,争相崛起的几个欧洲强势王国之间的地缘厮杀已经越出欧洲地域,蔓延到新发现的大陆——不仅是美洲大陆,还有我国身处的东亚和内亚大陆。若要说施洛策的世界历史意识与他所属的政治体的地缘政治处境有内在关联,并非臆测。毕竟,对欧洲各国人来说,他们各自所属的政治单位一直处在激烈而且错综复杂的地缘冲突之中。严酷的生存处境让他们类似本能地懂得,“世界”从来不是和谐的“天下”,所谓Weltgeschchte[世界历史]不外乎各种政治体之间的地缘冲突史。 在写于年的一篇世界史短论中,施米特开篇就说: 我们身处的中欧生活在sousl’?ildesRusses[俄国人的眼皮底下]。一个世纪以来,他们内心紧盯着我们伟大的文化和制度。他们强大的生命力足以掌握我们的知识和技术,使之成为自己的武器。他们所秉有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勇气,以及他们正教的善恶力量无可匹敌。[9] 认识自己的远近邻人的禀性,是希罗多德所开启的世界史认识的基本原则。施米特所说的“一个世纪以来”,正是施洛策的《为孩子们准备的世界史》出版以来的年。当施米特写下这篇短论时,我国读书人大多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由于西方列强的煎逼,日本人很快学会了模仿西方帝国主义,积极掌握西方人的知识和技术,使之成为手中的武器用来征服中国。[10] 《新史学》呼唤新的教育意识年2月至年9月,为争夺对我国辽东半岛的控制权,日本与俄国在我国土地上打了一场典型的“世界史式”的战争。因为,这并非仅仅是日俄两国之间的战争,背后还有英国和法国在远东的角力,实际上是英日同盟与法俄同盟之间的战争。德国和美国正在崛起,为了各自的利益,美国支持日本,德国则支持俄国,即便当时德国与法国在欧洲仍处于敌对状态。 日俄战争(-)示意图 两个异国在我国土地上争夺地盘已经不是头一回。年6月,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站稳脚跟后,曾攻击葡萄牙人占据的我国澳门,以图夺取通往日本和我国台湾的海上交通线的控制权,遭葡萄牙的澳门守军用火炮给予重创。尽管如此,就战争规模而言,历时长达一年半的“日俄战争”仍算得上我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事。直到今天,我们对这场战争的成因、过程以及历史影响的探究远远不及日本史学界,颇令人费解。[11] 战争爆发之前两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报纸上发表了名噪一时的《新史学》(),史称我国现代史学意识的开端。[12]梁启超痛斥中国传统史书有四弊,根本理由是传统史学无助于中国“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 《新民丛报》创刊号 在笔者看来,这篇文章也理应被视为呼唤我国现代新式教育的标志性之作。毕竟,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指控明显带有改革传统教育的意图。他指责说,我国历代积累的史书已经“浩如烟海”,让人“穷年莫殚”: 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新史学》,页9) 梁启超并没有无视我国古代史书中蕴藏着政治智慧,问题在于,并非只要是读书人都能汲取这些智慧,遑论普罗大众。从古代史书中汲取政治智慧需要“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而这样的人古今中外任何时代都数不出几个。如今,非动员全体国民不能救国于危难,彻底更改史书的写作方式,编写全新的历史教科书势在必行。 结束对中国传统史书的针砭时,梁启超发出了迄今传诵不衰的呼吁: 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新史学》,页9) 这不也是在呼吁“新教育”吗?史界革命与教育革命是二而一的事情。首先,必须重拟史书内容;第二,必须为国民而非为少数人写史,这意味着必须普及史学教育,“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国民”,要让“臣民”成为“国民”,就得凭靠新式教育塑造“国民”意识。因此,梁启超有理由认为,新式教育的第一要务是改变史书内容和书写方式施行“国民教育”,否则,“声光电化”之类自然科学知识只会培育出“世界公民”。 接下来的问题是:重述历史应该依据何种史学原则呢? “进化论”漫画 梁启超概述了他从西洋人那里听来的人类“进化说”,即人类进化之公理在于“优胜劣败”。在任公看来,这种公理已经得到世界历史的证明,而中国史书却从未涉及这样的公理: 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实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夫群与群之互有所排也,非大同太平之象也,而无如排于外者不剧,则结于内者不牢;结于内者不牢,则其群终不可得合,而不能占一名誉之位置于历史上。(《新史学》,页16) 在今天看来,梁启超所表述的“进化论”史观太过粗糙,也太过质朴。但他受时代的知识语境局限,我们不必苛求。我们倒是值得注意这里出现的“世界历史”这个语词,因为它表明梁启超的头脑已经有一种世界史觉悟,而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对他的这一觉悟给与足够的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旧闻新说ldquo广州rdqu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